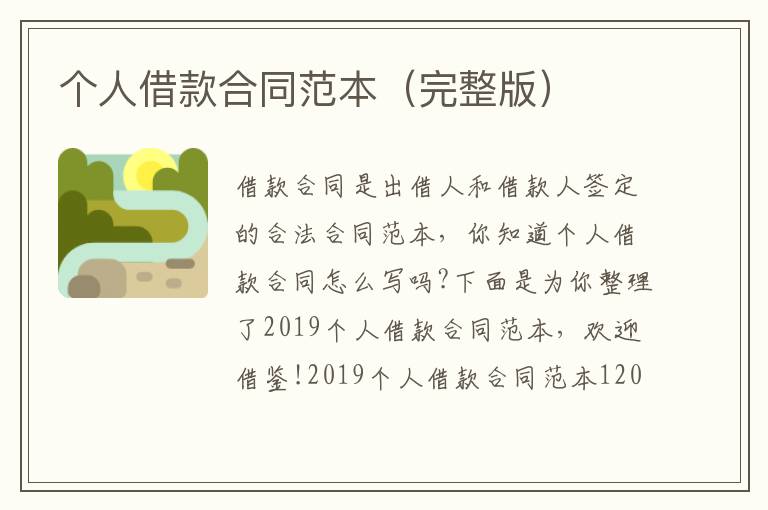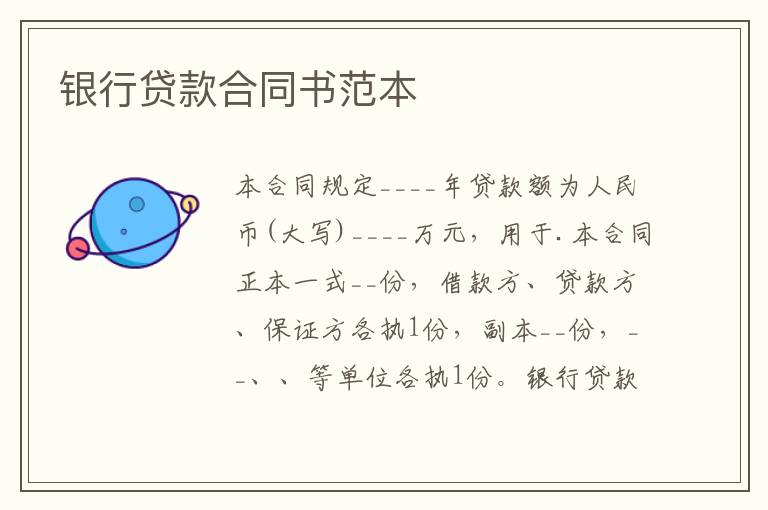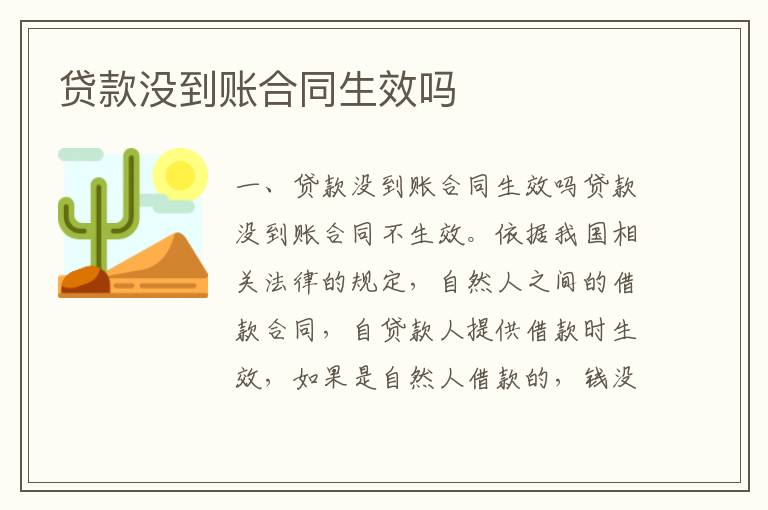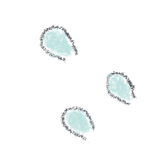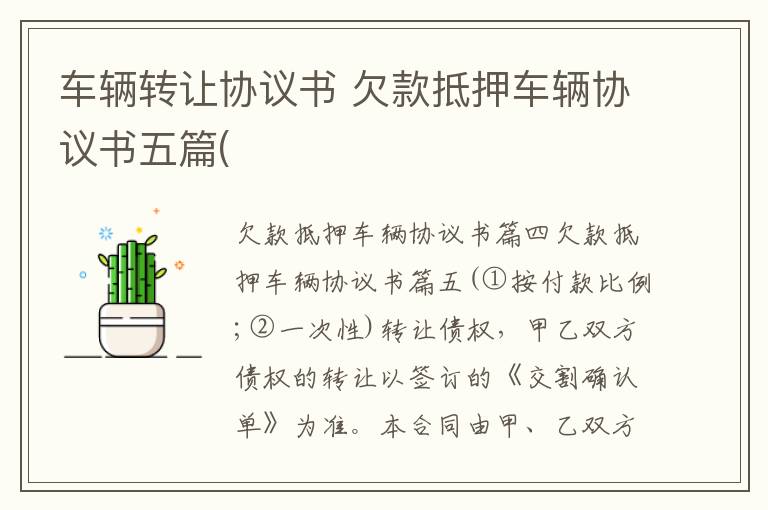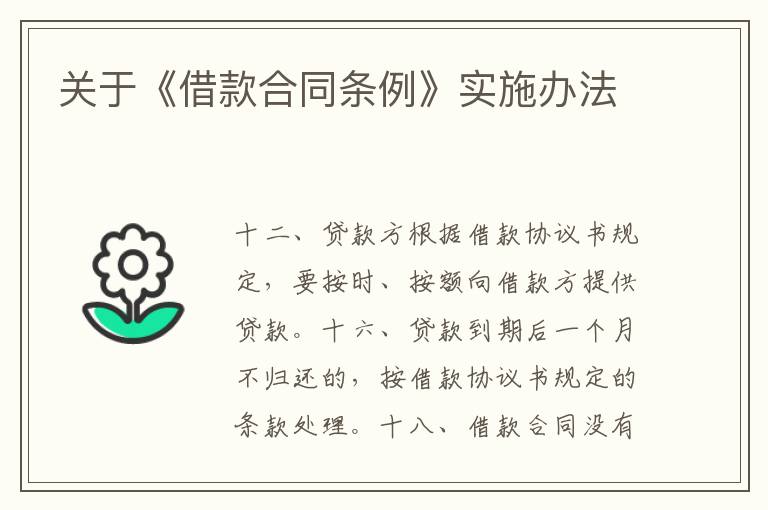【简介】感谢网友“网络”参与投稿,这里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方便大家学习。
流押契约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在订立抵押合同时或债权清偿期届满前,约定债务人届期未履行债务时,抵押物的所有权即归抵押权人所有的协议。流押契约虽然可以大大节约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的成本,但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均对此进行了明文禁止。
有关规定:
《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不得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
《担保法》第四十条: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
《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七条: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约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的内容无效。该内容的无效不影响抵押合同其他部分内容的效力。
流押契约主要有以下特征:(1)在时间上,流押契约的达成是在设立担保时或债权清偿期届满前;(2)流押契约一般建立在抵押权存在的基础之上;(3)从对象上看,流押契约针对的是抵押物的所有权归属;(4)在法律效果上,若债务人未能按期偿还债务,债权人则可直接取得抵押物。最后,从法律评价的角度,《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五十七条明文规定,流押条款应属无效。该条及物权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和担保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均体现了公平、等价有偿原则,避免债务人为情势所迫,提供价值较高的抵押财产担保价值较小的债权。
节选自(2017)沪01民终688号案判决意见:
周某在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的同时,委托马世明出售系争房屋,系以合法形式掩盖设立流押条款的非法目的,故该授权行为无效。理由如下:我国法律关于禁止流押的规定是为了体现民法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避免债务人为情势所迫,提供价值较高的抵押财产担保价值较小的债权,在担保物权实现时,债权人不但取得其债权所对应的价值,还额外获得抵押财产的剩余价值,损害抵押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在实践中,既存在典型的流押条款,也存在各种表现为合法形式的变体的流押条款。本案中,从委托的目的来看,洪程与韩某、周某之间的《借款合同》,洪程与周某之间的《抵押合同》,韩某、周某向马世明出具的《委托书》于同日签订、于同日办理公证手续,三者之间明显存在关联。马世明与周某互不相识,双方既未曾就委托事宜进行过协商,也未曾就房屋出售事宜发生过联系,马世明收取购房款后转交给洪程而非周某。上述委托授权显然并非为被代理人周某的利益设定。马世明称,签订《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时已告知对方如不能还款就出售系争房屋,无论“告知对方”一节事实是否成立,从其陈述中可以推知,债权人要求周某、韩某签订《委托书》的目的系为取得系争房屋的处置权,以便于其不通过法律规定的折价、变卖、拍卖等形式,变通地实现抵押权。本案中,马世明代为出售系争房屋时,未与周某取得联系,也未与周某商议房屋售价,最终也未将购房款转交周某。综合考虑委托的内容和其实际履行的结果,此种脱离了被代理人控制的全权委托,使得周某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时,已丧失对系争房屋的处置权、议价权和对剩余价值的取回权,其所有权被抵押权架空,实质上侵害了禁止流押条款所保护的法益。综上,法院认为该授权行为无效。
从上述案例的判决意见可知,流押条款之所以会被认定无效,主要是其剥夺了抵押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时,根据当时市场交易价格,通过公平议价的方式确定抵押财产价值,并收回剩余价值的权利。而以房抵债协议大多是为了担保原债的实现,在债务人未能按期偿还债务,债权人通过以房屋折抵债务的方式实现债权,该种折抵有可能出现与流押契约相似的结果,均会导致双方利益失衡,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因此,有学者认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的以房抵债合同实质是流押契约。小编认为,虽然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前的以房抵债协议与流押契约都具有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也均发生在债权清偿期届满前,但并不能将两者完全等同视之。
节选自(2018)吉02民终1694号案判决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林地转让协议约定,如马玉芹在借款期限届满时不能偿还借款,马玉芹以其承包经营林地抵偿借款及利息,是否属于流押条款。本院认为,清偿期限届满前的以物抵债协议与流押条款在本质上存在不同。流押条款是担保合同中抵押的条款,而以物抵债协议一般是对债的履行的变更。流押条款中的物为抵押或者质押物。以物抵债协议中的代替物是债的履行标的,且以物抵债协议中物的价值约等于债权数额。就本案来说,第一,2017年3月14日各方在签订林地转让协议书时,王立国的债权并未到期,双方约定以林地转让款抵顶欠款及利息,同时协议书中还约定如债务履行期届满前马玉芹能够偿还债务,林地转让协议解除,从上述约定中可以看出,以林地转让款抵偿欠款并非是变更了债务履行的方式,而是担保债务的履行。同时,王立国在二审庭审时亦自述系“拿林地作抵押”。第二,协议中虽约定以林地转让款抵顶借款本金及利息,但双方对于借款本息的数额并未核算,对林地转让款的数额也没有明确,故双方就债权实现中并未对抵押物的价值进行折价、清算,难以认定王立国的债权数额与马玉芹14.9公顷的林地承包经营权价值相当。第三,王立国上诉主张马玉芹对林地并非享有所有权,其转让的也非所有权而是林地经营权,故不适用于流押条款的规定。本院认为,我国法律禁止流押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关系,防止债权人利用优势地位获得大于债权的利益,这一利益不应仅限于物之所有权,也应包括其他的财产性权利,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中的“所有权”作扩大性解释,符合我国法律禁止流押条款的立法宗旨。
上述案例中,人民法院从以物抵债协议与流押契约的不同之处出发,最终认定林地转让协议属于流押契约而无效。总体而言,以房抵债协议与流押契约主要存在以下不同:
01
存在前提不同。流押契约建立在抵押权存在的基础之上,而以房抵债协议一般要求存在原债即可,并不以抵押权的存在为前提。
02
法律后果不同。在流押契约的情形,若债务人未能按期偿还债务,债权人可直接取得抵押物;而以房抵债情形下债权人并不能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权。
03
目标导向不同。流押契约设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而以房抵债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所达成的,目的是为了担保原债的履行。
04
债务人的地位不同。流押契约设定时,债务人通常处于劣势地位,债权人利用债务人窘迫之情形,以价值较高的抵押物担保小额债权,从而谋取暴利;而对于以房抵债来讲,原债产生的基础并非仅仅基于借贷关系,该债务的发生形式多样,债务人未必处于劣势地位,且房屋与债权额多数情况下价值相当,债务人以价值相当的标的物折抵原债,不属于流押契约。
综上,以房抵债与流押契约在本质上存在区别,两者并非同一概念。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以房抵债协议是否违反流押禁令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但总体而言,面对个案的具体裁判时,应结合具体案情,考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充分把握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如此方能不与法律规则的设定初衷相背离。